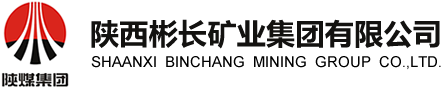文艺生活
前天,母亲从塬上下来看我,带来了苜蓿菜饼。
“都这个月份了,苜蓿花都开了吧,你是从哪里弄得苜蓿芽?”我好奇的问。
母亲笑着说:“我看天快要下雨了,就跑到山上把苜蓿割了一片,雨过后五天就长出了嫩芽。”
我心底涌上暖暖的感觉,口中的菜饼香味也更浓了。
我生长在农村,从小就和苜蓿打交道,春天掐苜蓿芽,夏天割苜蓿,秋天晒苜蓿,冬天铡苜蓿,一年四季都与之生生相息。
奶奶对我说过,苜蓿会说话。我当时笑着问:“那苜蓿都说些什么?我怎么什么也没有听到过?”
奶奶说,她很小的时候,大家还都吃的是“大锅饭”,苜蓿可是稀罕物,受公社管理分配,掐苜蓿跟分粮一样,有领票制度。尤其“那几年”,大家都在传要跟“老毛子”打仗了,收的粮食大部分要上交国家,大家都勒紧裤带过日子,吃不饱是“家常便饭”。她母亲经常挖野菜树根回来充饥,但那苦涩的味道实在难以下咽,好不容易领到苜蓿票,也得等家里来了亲戚去掐些苜蓿芽回来招待客人。随后三年,全国各地遭遇大旱,她们村也没有幸免,麦苗活活被晒枯在田里,但苜蓿由于耐旱性强,面对老天爷的无情考验,依然坚韧生长。
有一次,奶奶实在受不了野草树根做的饭,就去偷苜蓿。摸着黑来到苜蓿地,不分柴草,揪住就往笼子里扔。她记得清楚,当时,天空中挂着一轮白白的月亮,直直的盯着她,她小心翼翼蹲在地上,迎着风,以便看守的人来时她能及时发现。没过多久,她突然听到一个轻微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,“小娃,赶紧跑吧,看守的人马上来了。”她吓得一激灵,急忙回头,什么人也没有,环顾四周,还是一个人影也没有,只有苜蓿在风中摇着头。她吓坏了,提着笼撒腿就往回跑。
回到家,父亲问她苜蓿是从哪里来的?她自豪地说,是她偷来的,以为父亲会表扬她,没想到父亲脸色大变,把她狠狠地揍了一顿,说:“苜蓿是国家的,怎么能偷呢?”让她母亲还回去,她母亲不答应,连她母亲也被揍了一顿,但她母亲还是将苜蓿做成了饭菜,她父亲倔强的一口都没有吃。尽管那时候苜蓿已经很老了,但还是被她兄妹几个狼吞虎咽地吃完了。
她后来把那晚在苜蓿地遇到的事讲给她母亲听,母亲说:“那是苜蓿给你说的,怕你被抓住了挨批斗。”从那个时候,她就知道苜蓿是会说话的。
我对苜蓿最深的记忆,是每年惊蛰过后,苜蓿就像过完了冬眠的昆虫一样,从地里钻出来。尤其向阳的地方,苜蓿能最先嗅到暖阳的味道,探出小小的嫩绿的脑袋。
每年,还没等到山上春雪消融完,奶奶就开始往山上跑,等苜蓿芽一冒出来,就喊着我们去掐苜蓿。当然,每次都有人比我们来的还早,大家成群结队,欢声笑语,荒寂的山坡上一下热闹起来。
刚出来的苜蓿芽太小,掐起来很费神,要蹲在地上。奶奶年纪大了,蹲一会儿就腿疼的厉害,就只能跪到地上去。
奶奶每年做好苜蓿饼都要给叔叔捎过去,多年如一日,即便叔叔如今在西安已经有房有车子,经济状况还算可以,但她依旧坚持不懈,她坚信苜蓿会把她对儿子的思念和爱如数讲给儿子听。
上小学时,国家开始重视生态环境治理,推行“退耕还林”政策,降低水土流失,要求每家每户把劣质土地种成苜蓿,发放种子和苜蓿专项补助。因此,我们家的苜蓿地也多了起来。苜蓿生长周期短,割掉一茬后,不到一个月又会重新长出来一茬,割苜蓿也成了我暑假最常干的一件事。
苜蓿开出紫色的花,像葡萄串一样,甜甜的,会招惹来很多昆虫。夏天的午后,五颜六色的蝴蝶在苜蓿地里翩翩飞舞,我们追着蝴蝶嬉戏打闹,会被浓密的苜蓿绊倒,于是,我们干脆在苜蓿地里打滚,母亲呵斥无果,便吓唬我们说,苜蓿地里有蛇,我们便四散逃掉。
现如今,大家都奔忙在外,尝遍了外面世界的山珍海味,最怀念的还是家乡的饭菜,尤其,那一把苜蓿,会做成菜饼、菜疙瘩、调成凉菜、下到汤面里……香味在唇齿间久久不能散去。为生计忙碌奔波的人,为吃一口苜蓿菜,回一次老家,到底是划不来。然而,从超市买回去,做出来却总是另外一种味道。记忆里,父母端上苜蓿做成的饭菜,香味便迎面扑来,蘸上酸辣汁,咬上一大口,那柔软的清香味,透心沁肺,黏在手指上的残渣,也要舔干净。
人都说苜蓿身上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奉献精神,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,都能如期长成。从嫩苗时就开始被做成各种佳肴,夏秋时即便被一茬一茬收割,但依旧能茎叶茂盛,直到根部被挖出来铡成草料。
苜蓿说,人们说的都不对,它只是要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,即便远离故乡两千多年,它都不曾忘记那个又冷又旱、黄沙漫天的西域,它始终把对故乡的思念深深的刻在基因里,讲给风听、讲给雨听、讲给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听。
历史滚滚向前,苜蓿的语言留在几代人的记忆里,成为一抹独特的风景。我喜欢听苜蓿说话,喜欢它说很久很久以前……
编辑:达文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