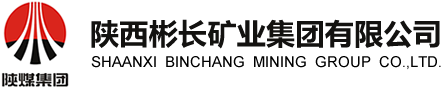文艺生活
“又是一年三月三,风筝飞满天,牵着我的思念和梦幻走回到童年。”许是连日的好天气,再加上刚刚进入的三月天,大清早心里就默默哼唱起这首歌。或许对童年的记忆,三月是最深刻、最难忘的吧。
泾河边,远眺对面的山,还是有点苍凉。唯一不同的是山下面的那两条公路。新路两侧的柳枝隐隐透着绿,大小车辆来来往往,车流嘈杂声却也让人心生几分不宁静。幸好,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条过去的老路,已有些荒废。附近的老人说,这是彬县最早的一条公路,是古“丝绸之路”必经之地,是连接长武、甘肃的交通要道,后来又修了前面的新路和高速,以前熙熙攘攘的老省道就变得无人问津了。
走在古道上,怀想着三千多年前后稷生地,公刘故里历经了多少沧桑才产生了《诗经•豳风》这部不朽诗篇,也让范仲淹、李白、杜甫等文人墨客留下了咏彬诗句,被后人千古传诵。再看山下建于唐代的大佛寺,有着“关中第一奇观”的美誉,寺庙每年三月初八都会举办一年中颇为盛大的庙会,特色小吃、民俗民风、各种表演承载着多少人的童年欢乐。
这边恋旧的人家还在半山或山上留有一房小院,有的已经随着时间慢慢破旧下来,但是,并不妨碍暑假回来的学生娃们嬉戏玩耍。
路的远处,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手牵着一只风筝跑了过来,风筝飞的不高,离地也就二层楼高。小一点的跟着跑,开心的喊着“飞起来了,飞起来了”。风筝很精致,形似如鹰,那孩子手上拿的线轮很密实,应该是那种能放很高很高的那种。无奈,他跑的不快再加上风向不对,风筝慢慢落了下来。又试了几次,还是飞不起来,索然无味的两个孩子拿着风筝往山上跑去。
这只精致的风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。十来岁时,家属院里年龄相仿的男生每到正月里就会不时地聚一起做风筝,然后选一个阳光好、有风的天气,到附近的铁路涵洞上放风筝,女孩子想参加那是不可能的,不甘心的我们也会远远跟着。但是,通往涵洞的路上那条又宽又深的沟成了我们的障碍。所有的好奇和不甘心只能让我们远远看着。
男生们自制的风筝,多是用报纸做成的,形状每年也会有变化,椭圆的、三角形、菱形的,出奇的是不管什么形状,都能飞得很高很高。据说,有一次几个人从家里偷拿的线连在一起都不够长,风筝最终还是“挣扎”着飞走了。
带着失落的心情回到家,想着大人们一定会做。可是,忙于生计的家长们哪有时间帮我们做这些“不管吃不管喝”的玩意。于是,要好的小姐妹商量,各自从家里拿材料。报纸、竹条、缝被子的粗棉线、剪子,这些很快就到位了,唯独没有胶水。一问才知道,男生用的是面熬成的面糊糊,粘得牢还不花钱。于是,我去求助母亲。缠了几天,母亲给做了一碗面糊糊。
兴奋之余,还是害怕第一次做不好,“威逼利诱”之下,请了做的最好的男生帮忙。设计画线裁纸、竹条削整捆绑、棉线对接绕团……几道工序下来,一个半米大小的菱形风筝糊好了,把剩下报纸的边角裁成五六厘米宽的长条,几段糊在一起做上两条,粘在风筝的下端当作尾巴。最后,居中找准绑线的地方,上下左右各拉一根线,形成稳固状态后,风筝就做好了!
第二天一大早,起床后先跑出去看看有没有风。真好,天气晴朗伴有微风,七八个小姐妹集结一起向涵洞出发。终于费尽周章爬到男生以往放风筝的地方,才发现这个地方是个风口。一点点松开线团后,我们的风筝顺势就飞了起来,几个女孩子高兴地喊个不停。慢慢我们发现那点线团真的不够用,想把风筝收回来。但是,风筝顶着风怎么也收不回来,力气大的赶紧接手,猛拽之后风筝失去了平衡,左一下右一下摇摆起来,然后就开始剧烈的转圈圈,线很快绕在了一起。看到这种情况,大家都慌了,只有在下面当观众的那个男孩子说,放手,快放手。于是,那个写满我们名字的风筝飘走了,留下了哭的七零八落的我们。
就这样,我们打破了只能男生做风筝、放风筝的惯例,也多了一些合作,男生制作,女生用蜡笔涂上喜欢的颜色,男生凑不够的线团,女生也想办法。终于,放风筝成了那个时期每年三月必须要做的一项活动。
当然,这个三月里,我们也会偷偷去麦田拔一把刚长出嫩叶的麦苗回去喂兔子;也会抽几根菜农家的长竹条作鱼竿去踞水河里钓小白条喂猫;也会在作业没写完的时候偷偷跑出去挖野菜;也会十几个男女生混作一团跳皮筋、打沙包、翻嘎啦哈、弹弹珠。
那时候,童年的欢乐总是很容易满足。
再看远处,那只鹰形风筝飘起来了,是那家大人帮忙放飞的。年龄小的如同当年的我们一样,跳着拍着手,满眼都是快乐……(小庄矿 丁运华)
编辑:徐超